19世纪以前的课堂,大多是单调、重复、耗时的算术训练。德国布伦瑞克的一所小学里,一个普通的早晨,数学老师给全班同学出了个看似“磨时间”的题——把从1到100的所有整数加起来。
在老师的设想中,这是一道完美的拖堂题:100个数,乖乖从1加到100,别说是小学生,大人算起来也要好一阵。可事情没有按剧本发展——还没等粉笔在黑板上写完题意,一个瘦小的少年就把答案报了出来:“五千零五十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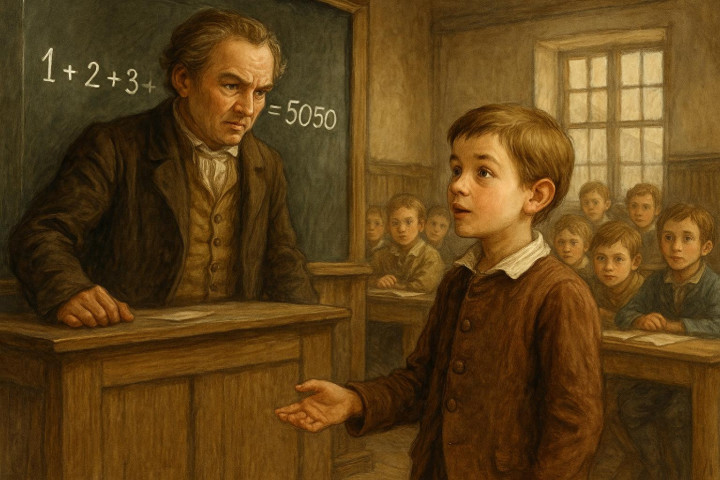
这个少年,就是后来被誉为“数学王子”的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高斯(Carl Friedrich Gauss)。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埋头逐个相加,而是抬起头,在脑海里“看见”了整个数列的规律。
他的思路是:把1和100配对,得到101;再把2和99配对,也是101;3和98,还是101。这样的配对一直持续下去——总共有50对,每对都是101。于是,总和就是50 × 101 = 5050。
不到一分钟,高斯就完成了老师原本要用半节课的“陷阱任务”。这一瞬间的灵光,直接孕育出一个通用公式:前n个整数的和 = n(n+1)/2。只要知道n,就能瞬间算出结果。
这个公式看似小巧,却藏着重要的启示:它不仅解决了有限数列的加法问题,还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通往“无穷”世界的大门——当n无限增大时,会发生什么?和会变成多大?那已经不是课堂小把戏,而是数学史上的深水区。
看似温柔的陷阱:调和级数的背叛
如果说高斯的故事告诉我们,“无穷”会让一个公式变得更加有趣,那么接下来的例子则证明,“无穷”也会让你的直觉彻底崩溃。
数学家们换了一个玩法:不再直接把 1、2、3、4……这些整数加起来,而是取它们的倒数——1,1/2,1/3,1/4,1/5……这就是著名的调和级数(Harmonic Series)。
乍一看,这个级数温柔得很:每一项都比前一项小,衰减速度肉眼可见。直觉告诉你,既然数字越来越小,累加的结果应该会逐渐趋向某个极限。
起初的确像是这样。第一项1,加上第二项1/2,总和是1.5;再加1/3,变成1.833…;加到第10项,也不过是2.928…——看起来快到“平稳区”了。更夸张的是,如果你想让这个和超过5,你得加上前83项;超过6,需要前227项;而要冲到10,你得耐心地把前1.2万项都加进去。增长得如此缓慢,很容易让人以为它最终会停下。
但14世纪的法国学者尼古拉·奥雷斯姆(Nicole Oresme)用一个精巧的分组方法,彻底粉碎了这个幻觉。
他把调和级数这样分组:
第1组:1
第2组:1/2
第3组:1/3 + 1/4
第4组:1/5 + 1/6 + 1/7 + 1/8
第5组:1/9 + … + 1/16
后面的组每次项数翻倍:16个、32个、64个……
看似随意的分组,却暗藏杀机:第三组中的每一项都 ≥ 1/4,所以这组的和 > 1/2;第四组每一项都 ≥ 1/8,这组的和又 > 1/2;第五组每一项 ≥ 1/16,这组的和依然 > 1/2……换句话说,除了开头的1,后面每一组都贡献了大于0.5的增量,而且这样的组是无限多的。
于是,调和级数的累加过程就像走楼梯——每走几步,就稳稳地上升半个台阶,永远不会停下。
结论无情而震撼:即使项越来越小,调和级数的总和依然会在无穷中失控地增长。数学家称它发散(Diverge)。
而这场“温柔陷阱”背后的逻辑,正为后来的一个问题埋下伏笔,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能收敛的无穷和?
第一道“驯服”的无穷和:三角数倒数
17世纪的欧洲,数学家们已经在无穷的海面上航行了一阵子。调和级数的背叛让他们警觉:不是所有看起来“越来越小”的数列都会乖乖收敛。但那也激发了一个新的好奇——有没有一种无穷加法,真的能“收口”到一个有限值?
荷兰科学家惠更斯(Christiaan Huygens)就抛出了这样一个挑战:把“三角数”的倒数加起来,会发生什么?
所谓“三角数”,是一种用圆点排成等边三角形的数字图案。
第一行1个点,是三角数1;
再加第二行2个点,总共3个点,是下一个三角数;
第三行3个点,总共6个点;
接着是10、15、21、28……
它们的数学公式很简单:第n个三角数 = n(n+1)/2。
惠更斯的问题是:把它们的倒数加起来——
1/1 + 1/3 + 1/6 + 1/10 + 1/15 + ……
这串无穷和,会不会收敛?如果收敛,又收敛到多少?
年轻的莱布尼茨(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)接下了挑战,并很快发现了一个绝妙的拆分技巧。
他先写出这个和:
1/1 + 1/3 + 1/6 + 1/10 + ……
然后观察公式 n(n+1)/2,把分母里的n和n+1拆开,发现每一项都可以写成这样的差:
1/1 = 1 − 1/2
1/3 = 1/2 − 1/3
1/6 = 1/3 − 1/4
1/10 = 1/4 − 1/5
……
神奇的事情发生了:当你把这些项一项一项加起来,所有“中间项”都会前后抵消——1/2被减掉又加回来,1/3也是如此,1/4也是……唯一幸存的,是开头的那个“1”。
结果,整个无穷和在抵消之后,只剩下:
S/2 = 1
于是,S = 2。
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它告诉数学家们:无穷相加并非注定失控,只要衰减得够快、结构足够巧妙,就能收敛到一个确定的值。
而且,莱布尼茨的方法给了他们一件新武器——通过结构拆分和连锁抵消,驯服原本看似不可控的无穷级数。
接下来,这件武器很快就被用在了一个更大、更棘手、也更传奇的问题上——巴塞尔问题。那是一头沉睡百年的“数学怪兽”,直到遇见一位史上最强的大杀器:欧拉。
巴塞尔问题的百年之谜
如果说三角数倒数的收敛给了数学家信心,那么下一个挑战,则让他们一次次撞在了无形的天花板上。
这一次,分母不再是三角数,而是平方数:
1/1² + 1/2² + 1/3² + 1/4² + 1/5² + ……
这些数字看上去比调和级数要“温顺”得多——衰减得快得多,而且和三角数倒数一样,项与项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。于是大家猜测,这个和肯定是有限的。
证明它收敛并不难。17世纪末,瑞士数学家雅各布·伯努利(Jacob Bernoulli)就用“比较法”做到了:
既然三角数倒数的无穷和是 2,而平方数倒数的每一项都比三角数倒数对应项更小,那它的总和一定小于 2。
问题在于——它究竟等于多少?
雅各布没能找到答案。他甚至在论文末尾写下了公开求助:“如果有人能找到这个值,并告知我们,我们将不胜感激。”
从那一刻起,这个看似无害的问题,就像一枚火种,在欧洲数学界悄然发酵。由于雅各布来自巴塞尔,这个谜题被称作“巴塞尔问题”。
它的表面很简单:
但简单的外衣下,藏着的是数学的硬骨头。你可以算前10项、前100项,得到一个越来越接近的数字——1.549… 1.634… 1.643…——它似乎在逼近某个神秘常数,可它就是不肯“自报家门”。
伯努利家族的另一位天才——约翰·伯努利(Johann Bernoulli)——也没能破解。更让人绝望的是,莱布尼茨、惠更斯等一线高手也束手无策。一百多年间,没人能找出确切的闭合公式。
巴塞尔问题成了数学家的集体执念:它没有奇怪的定义,没有复杂的背景,只是赤裸裸的“加一串分数”——可这串分数,就像有魔咒一般,把所有聪明人挡在了门外。
直到18世纪30年代,一个年轻人拿起了它。
他出身巴塞尔,数学启蒙老师正是约翰·伯努利本人;他才二十出头,就已经在数学前沿发光发热;他的思维天马行空,不受旧方法的束缚——他叫莱昂哈德·欧拉(Leonhard Euler)。
而他,正要用一次惊天的跨界联想,让巴塞尔问题的百年迷雾,在一瞬间化为清晰的阳光。
欧拉的惊世一跃
1730年代的巴塞尔,莱昂哈德·欧拉年仅二十出头,刚从伯努利兄弟的课堂毕业,便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闯进了数学的核心战场。巴塞尔问题,这个困扰欧洲数学界百年的死结,在他眼中不是绝壁,而是通往高峰的阶梯。
欧拉没有沿用前人那套“对比、夹逼、近似”的老路,而是转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——把这个加分数的问题,和一个三角函数扯上关系。
他从正弦函数 sinx 出发。学生时代的他早已熟练掌握泰勒展开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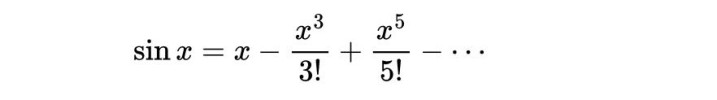
于是,(sinx)/x 就是一个关于 x^2 的无限多项式。
另一方面,他又想起了代数中一个简单但威力巨大的事实:一个多项式可以分解为与它的“根”相关的乘积。比如,一个二次多项式 P(x)有两个根 a 和 b,它就可以写成 (1−x/a)(1−x/b)的形式。
如果多项式可以这样分解,那无限多项式呢?欧拉凭着惊人的直觉,认为这同样适用于(sinx)/x这样的“无限多项式”。
正弦函数的零点大家都知道:除了 x=0,其余都是 ±π,±2π,±3π,…。于是欧拉将 (sinx)/x 写成了一个惊人的无限乘积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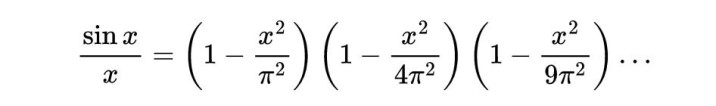
接下来是魔术时刻——他把这个乘积“假装”像普通多项式一样展开,比较两边的 x^2 项系数。
一边是泰勒展开的 x^2 项系数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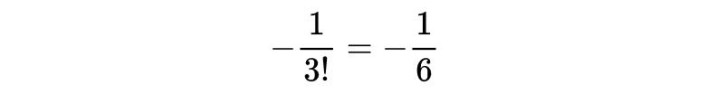
另一边是无限乘积的 x^2 项系数:它来自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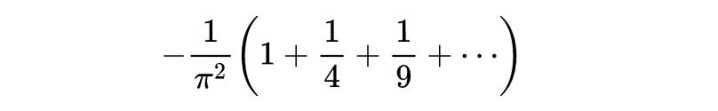
让这两个系数相等,负号对消,结果震撼人心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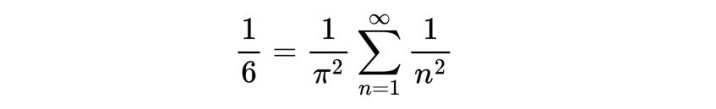
于是—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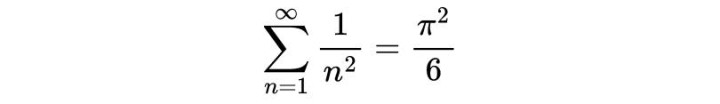
巴塞尔问题的百年迷雾,在一瞬间被刺破。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圆周率 π,竟然深藏在整数平方倒数的和里。
1735年,欧拉公布了这个结果,数学界轰动不已。雅各布·伯努利早在几十年前的感慨“若有人找到答案,我们将不胜感激”,终于等来了回音,而且答案的美,超乎任何人的想象。
更令人惊叹的是,欧拉并未止步于此。他用同样的方法,找到了所有偶数次幂的倒数和公式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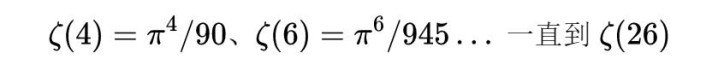
而奇数次幂的倒数和,却像一道新的铁门,至今没人找到它的钥匙。
未解的另一半与黎曼的远方
欧拉的胜利,不只是解开了巴塞尔问题,它更像是在数学世界里炸开了一枚信号弹——无穷级数的背后,潜藏着比想象中更宏大的结构。
用他的手法,所有偶数次幂的倒数和都被一网打尽,每一个偶数次的公式,都是干净到近乎诗意的分数,分子里安然坐着一个偶数次的 π,分母则是一连串整齐的常数。
可一旦幂次变成奇数,画面就变了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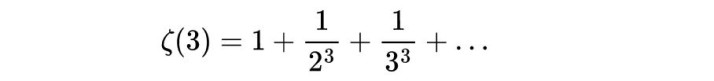
这就是著名的阿佩里常数(Apéry’s constant)。欧拉同样写得出它的数值近似,可等式右边却没有出现任何像 π^2/6 那样的简洁表达。几个世纪过去,它依然没有优雅的闭合公式——不仅 ζ(3)如此,ζ(5),ζ(7)等等全都顽固地沉默着。
数学家逐渐意识到,这些和式并非一盘散沙,而是属于一个更庞大的家族:黎曼 ζ 函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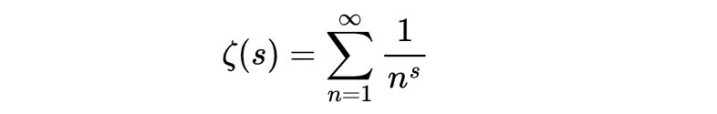
这里的 s,可以是任何复数。当 s 是偶数正整数时,欧拉的成果闪闪发光;当 s 是奇数正整数时,它们则像深海里的暗流,不肯向人类吐露全部秘密。
1859年,德国数学家伯恩哈德·黎曼(Bernhard Riemann)在一篇不到十页的论文中,将 ζ 函数推进到了一个更惊心动魄的维度——他把它延拓到了整个复平面,并在分析它的零点分布时,提出了一个至今无人攻破的猜想:黎曼假设。
黎曼假设看似离巴塞尔问题很远,但它触及的却是同一根神经:素数的分布。ζ 函数的性质,与素数的规律紧密交织在一起。若黎曼假设成立,我们将能以近乎外科手术的精确度刻画素数的出现节奏。这不仅是数论的皇冠,更被誉为数学界的珠穆朗玛峰——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为它悬下了一百万美元的悬赏。
从高斯课堂里的 1+2+…+100,到欧拉手中的 π^2/6,再到黎曼 ζ 函数延伸出的世纪难题,这条路横跨了两百多年,串联起无数数学家的心血与执念。
偶数幂的答案,像白天的星星,已被看得清清楚楚;奇数幂的谜团,依旧在夜色里沉睡。而那片夜色深处,也许正藏着数学未来最炽热的光。